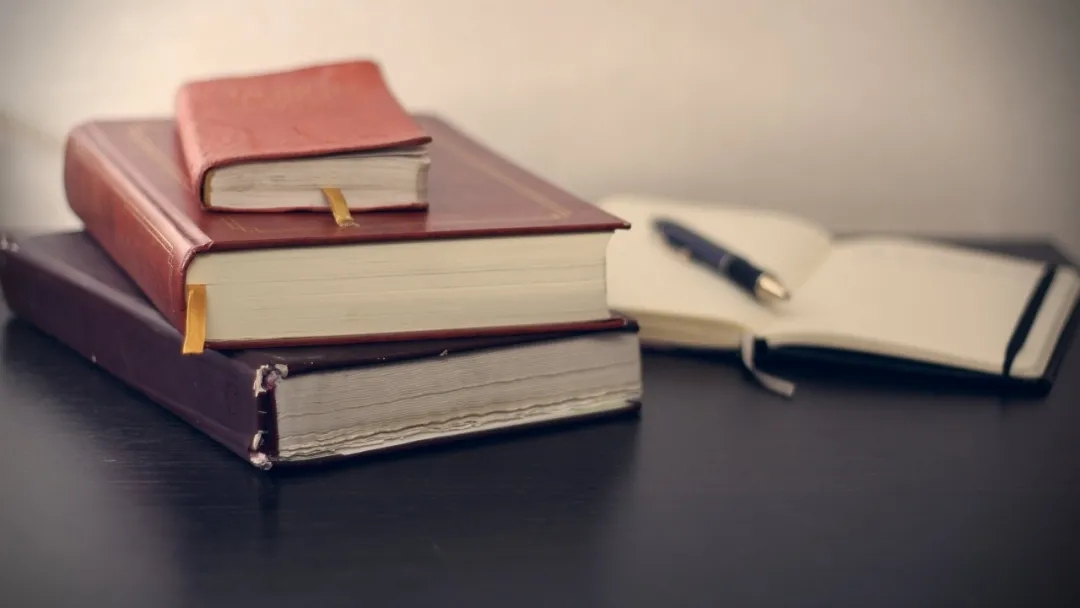浅议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对象认定问题
发布时间:2021-06-08 作者:
专注领域:民商事诉讼仲裁、企业合规、不良债权处置与困境企业拯救。
环境违法事实的发生,有时会涉及多个主体,常易发生处罚对象认定争议。本文从一假设案例出发,讨论其中的部分争议。假设案情如下:自然人A系船主,受某土石方工程公司雇请,装载并倾倒疏浚淤泥。经执法人员查明,A驾船在海上倾倒淤泥但倾倒作业地与其出示的《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副本)规定的位置不符合,实际倾倒作业地并不在指定允许的倾倒区域内。本案的废物倾倒申请单位为某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港口公司),港口公司进行淤泥疏浚,通过招标由某港建工程公司(以下或简称工程公司)施工,而工程公司又把工程转包给一土石方公司,A系受土石方工程公司雇请进行淤泥倾倒。观点一:港口公司应为处罚对象,因其系《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的申请和持有人,作为业主是该倾废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倾废船只是为其雇主单位做事,在出现违法行为时被许可人即港口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观点二:船主A应为处罚对象,理由是倾废系其个人行为,未受到港口公司许可或受其指使。观点三:船主A是主要责任人,应为处罚对象,但如遇到船主逃逸,住所地不明,执行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处罚港口公司。1、《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按照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废弃物装载之后,批准部门应当予以核实”。(以下或简称第59条)2、《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不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倾倒,或者向已经封闭的倾倒区倾倒废弃物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以下或简称第85条)3、《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如下:四、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处以人民币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不按批准的条件和区域进行倾倒的,但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不在此限”。(以下或简称第20条)4、《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违反《条例》和本实施办法,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海区主管部门可依照《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未获得主管部门签发的倾倒许可证,擅自倾倒和未按批准的条件或区域进行倾倒的,按《条例》第二十条有关规定处罚”。(以下或简称第34条)
第85条、第20条、第34条作为处罚规定条款并未明文规定处罚对象,但与该条中“不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倾倒”中相关联的规定“必须按照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第59条)结合,可判定按许可证倾废的行政法上义务人应指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在法律对某种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设定的行政处罚条文中,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处罚对象(这应该比较常见),处罚对象认定应考虑除处罚条文之外的其他规定,具体判断行政法上的义务人,应结合其行为认定行政义务人为处罚对象。当然是否能够进行行政处罚,还需考虑一般行政处罚要件,比如与有责性相关的责任要件,与此相关条文通常规定在行政处罚一般法中,比如2021年7月1日起即将施行的新《行政处罚法》(以下或简称《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进而言之,假设行政处罚一般法中,对行政处罚对象做了扩张,比如规定了共同违法条款,则除前述行政法上义务人之外的故意共同实施者,也可成为处罚对象,共同违法条款指类似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4条的规定,具体内容为: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者,依其行为情节之轻重,分别处罚之。前项情形,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其无此身份或特定关系者,仍处罚之。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致处罚有重轻或免除时,其无此身份或特定关系者,仍处以通常之处罚。
根据前述关于行政处罚对象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船主不是未按许可倾废违法行为的处罚对象,现行行政法并未有可适用于该领域的共同违法行为条款1,尽管船主是违法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其也有可能成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直接责任人而被另案处理,但是就本案处罚对象只可能是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即港口公司。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港口公司并不是具体倾废实施者,船主未按许可倾废看上去也和港口公司没有关系(注:通常情况下,港口公司并不知道船主会未按许可倾废,也不会指使其未按许可倾废)。因此,违法行为归责于港口公司当如何解释?如果港口公司提出没有主观过错的抗辩,是否应当不予行政处罚?2抽象来看,该情形可归入这个问题:对于行政法上的义务人,借由契约(合同)运用第三人协助履行其行政法上义务的情形,原本负有行政法义务的人,其义务违反的主观过错该如何认定?对此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和司法实践似乎并未有深入讨论,更谈不上有清晰的法律规定。故以下从比较法角度出发来观察问题,试图借“他山之石”提供解决路径,主要参考台湾地区的“行政罚法”的理论与实践,具体为:1、台湾“最高行政法院”曾有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在“行政罚法”实施前裁处的,以类推民法(指台湾地区民法,下同)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解决3,并认为:人民由其使用人或委任代理人参与行政程序,扩大其活动领域,享受使用人或代理人之利益,亦应负担使用人或代理人之参与行政程序行为所致之不利益;在“行政罚法”实施后,按同法第七条第二项4,法人就其机关之故意或过失,仅负推定之故意、过失责任,人民就其使用人或代理人之故意、过失之责任,类推适用该“法”第七条第二项,负推定故意或过失之责任。52、就“行政罚法”第七条第二项“其他有代表权人”之解释,有认为包括意定代表人,比如受委托代表之律师、会计师等,凡实际上其于行为时享有私法人代表权者,均属之;另有观点认为,非关私法人、团体内部组织,借由契约运用第三人协助履行行政法上义务者,与该条文无关,其应回归同“法”第十条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6与第七条第一项关于故意、过失之责任条件的一般规定。7就“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事实之危险者”或“对发生违法结果之危险源有支配权限”者,关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其故意或过失的归责均不限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本身(盖此等行为通常由他人实现),应扩及于行为人从事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之前等活动,德国学理上以”承接上的过失“探讨此问题;对行政法上义务之违反是否有故意、过失,自应扩及于对违反防止义务是否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或因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违反防止义务之法律评价等同于积极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83、“行政罚法”第7条第2项不能类推使用自然人委任代理人情形;如义务主体和委任代理人有共同违法或本人行为已可构成行政罚之要件者,自当依其行为论责;委任代理人或使用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法规如对该等人设有处罚规定,则自当依各该规定论责,如未有设有处罚规定且未能依共同违法(指“行政罚法”第14条)予以论责者,则无从对于该等人裁处行政罚;此外,仍得视情况使义务主体对委任代理人或使用人之行为负一定责任:如委任代理人或使用人系以积极行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义务主体人可依据“行政罚法”第10条规定认本人系“依法负有防止义务”之人;如系以消极不作为违反的,义务主体人本人即应作为,可认为本人负有故意或过失致违反行政法上作为义务,而论其责任。9借鉴上述,具体回到本案解决,因港口公司借由第三人协助其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导致未按许可要求倾废违法行为发生,现行法下考虑归责于港口公司的可采路径有二:第一、“视同说”,即将船主之故意视同港口公司的故意,如前述台湾“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在“行政罚法”实施前裁处的,以类推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解决,采用的就是“视同说”;第二,“选任监督过失说”,如前述决议在“行政罚法”实施后,采用的推定故意、过失,但允许义务人举证其在选任监督上并无违反注意义务,推翻上述故意过失之推定。相比较二者,“选任监督过失说”较为合理,其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精神契合,较有现行法上的支持,也符合义务人本身不是具体行为实施者的身份,并且从《海洋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说,第59条其实指明了适用该条的对象是“单位”,因《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将“单位”和“个人”进行区分(第2条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所以不论是从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的方法,抑或是从不宜对有歧义的法律条文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考虑,该法第59条中的“单位”一语不宜扩张解释为“单位以及个人”,因此,从选任或监督角度考察其过错更为合理。另,由于《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均无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律规定,借“不纯正不作为犯”说法解决此问题在现行法上过于牵强,不宜采用。环境违法行为涉及多个主体而易发生认定处罚对象争议情形还有:1、委托运营情形:排污单位将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委托第三方进行运行管理,而第三方故意或疏于运行维护,导致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类似情形有污水处理厂委托运营后发生排放不达标污水;2、租赁经营情形: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在租赁经营模式下,建设项目的建设者将其项目整体出租给他人生产经营使用,若建设方未建成项目需配套的环保设施或者其建设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经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将造成承租人违法将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使用的情形;3、承包经营情形:承包他人的厂房设备以他人名义生产经营,发生违法排污行为;类似情形还有挂靠经营。就所述行政处罚对象认定问题,本文认为需综合考虑以下情况判断:2、一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法律是否对该等人设有明确行政处罚规定,是否已可构成行政处罚之要件;3、有无可适用的共同违法行为条款或其他规定可将行政处罚对象扩张至义务主体之外其他人;4、行政法上的义务人,借由契约运用第三人协助履行其行政法上义务的情形,义务人违法责任该如何认定,即本文假设案例所讨论。另,行政处罚对象与因同一违法事实而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限于篇幅和目前的学习深度,本文就行政处罚对象问题不再深入,将来再寻机专文讨论。[1]我国行政法中有适用与特定领域的共同违法行为条款,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但并未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置有普遍适用的共同违法行为条款。[2]此处按适用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考虑,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3]其引用的“民法”条文为:债务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关于债之履行有故意或过失者,债务人应与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负同一责任。[4]该文规定为:法人、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团体、中央或地方机关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权之人或实际行为之职员、受雇人或从业人员之故意或过失,推定为该等组织之故意、过失责任。[5]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第二版,元照出版社,第131-132页。[6]该第十条规定为:对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事实之发生,依法负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事实者同。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事实之危险者,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7]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第二版,元照出版社,第130-131页。[9]林锡尧著《行政罚法》,2013年最新版,元照出版社,第153-155页。
-a51b2428-cb13-4b38-991f-01645c35439a.jpg)